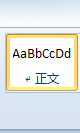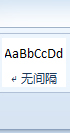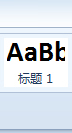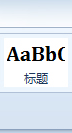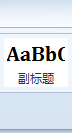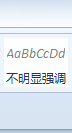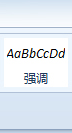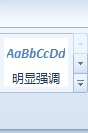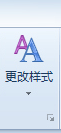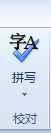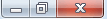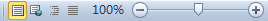到%确定
第十节 初中同学们的从业简况(下篇)
(接中篇)
一直在本村务农的有陈国章、闫庆华、金庆平、刘德富、崔合、杨德云、兰福林、郭春华、么克民、张连生、秦树余、刘忠贤、刘长泉、古宝春、王瑞庆、李文、苏中山、顾青、陈余、高永才、孟庆仓、单学良、张方、李树庭、杨久如、李天国等26人。
陈国章是下仓乡赵山庄村人,1965年7月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他在村里被推荐为赤脚医生,主要在本村医疗室上班,也曾经到县水利局的水利工地当“民技工”,做工地上的卫生员。
民技工是水利局从农村抽调的具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如施工中需要的木工、钢筋工、泥瓦匠、架子工等。这些人是水利建筑工地的技术工,他们常年跟随工程指挥部走,转战各个水利工地,而施工中需要开挖的土方工程和许多建筑小工,则是由各村临时摊派的社员。民技工和临时摊派的民工一样,也是有本村记工分,国家补贴部分伙食费。
1980年生产队解散后,各村的卫生医疗室也变成自收自支的小诊所了,陈国章还是当农村医生。农村医生虽然不是国家职工,但是在2002年后,国家允许民营企业职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和国营企业一样缴纳养老保险费,享受退休待遇。并且允许年龄大的补办缴纳前段上班时间的养老保险费,补交到退休前的十五年,俗称“一次性购买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于是陈国章就在本乡保险所补办缴纳养老保险费,购买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到了60周岁后,也和国家企业职工一样,领取了养老金,享受了国家企业职工的退休待遇,同时还在继续在家里当农医。
闫庆华是蓟县下仓乡王指挥庄村人,离校后回村务农,后参军入伍,服役期满后回村务农。他在村里当过几年村干部,生产队解散后,也在县城的酒店、旅馆等单位打工。1995年商品房市场开放后,闫庆华在城里买了商品楼房居住。现在他们老两口的户籍还在农村老家,也是在下仓乡办的农民养老保险。60岁以后,他们有了养老金收入,也就不再打工,而是在县城的楼房里颐养天年了。
金庆平是蓟县桑梓乡大卢庄村人,提前离开学校回村务农后,又参军入伍当了几年兵。也不知什么原因,他在部队得了精神抑郁症,退伍回家后,按照残废军人享受民政部门的照顾。因为他有病,自然也没有安排到工厂去当工人,而且在村里也算不上正常的劳动力,生产队只能给他安排些力所能及的轻松活,让他挣些工分。因他有病,连媳妇也没娶上。这样使他的抑郁症状有增无减,更没办法向正常人那样生活了。生产队解散后,工分没有了,他也分得了一份土地,有时也能到地里干些农活。大部分时间就是在村头和路边发呆,也不能和别人正常聊天。他的生活费还是国家民政部门发放,生活起居靠家里的亲属照顾。
金庆平在我们这些老同学中,是唯一没有结婚,没有成家立业的人。
刘德富是蓟县邦均镇西草场村人,1965年7月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一直在村里当电工,按月挣工分。那时在生产队下地干活的社员,是按每月出工的天数记工分的。在村里当支部书记、大队长、会计、农医、电工、看电话广播的等后勤人员是按月记工分的。农医和电工都是不需要下地干农活的。
1980年生产队解散后,村里的干部和后勤人员包括电工,只发给补贴工资,不给满工资。刘德富就不在当村里的电工了,受聘到本村办的民营工厂去打工,还是以电工技术为主,也兼做其他后勤工作。
他在民营企业打工十几年,企业不景气倒闭了。他们几个搞技术的打工者又几家合办了一个小厂子,他也当起了小股东。后来小厂子也不景气,停产了,他就买了辆机动三轮车,在邦均街上拉客人。一直到65岁以后,因体力欠佳,而且积攒的钱也够养老用了,就在家休息,颐养天年了。
崔合是蓟县官庄乡联合村人,提前离校回村务农,一直在本村干农活,有时也到附近做些轻松工作的小工。2007年开始,国家对年满60周岁以上的农民发放生活补贴,俗称“老年费”,同时对60周岁以下的农民实行购买养老保险政策。崔合在年满60周岁前夕,花一万九千元钱购买了养老保险。很快就享受了退休待遇,领取了社保公司发放的农民养老保险金,在家中颐养天年。2017年夏季,在家中突发心肌梗赛而亡。
杨德云是蓟县官庄乡石佛村人,1965年7月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在村里也被推荐当过赤脚医生。后来参军入伍,服役期满后退伍回家务农,在村里当干部。1980年生产队解散后,他辞去村干部职务,自己跑买卖、开公司。在经商过程中,曾因经济犯罪两次被判刑入狱。杨德云在部队服役期间,曾经到越南去参加抗美援越战争,为此享受国家对农村参战老兵的特殊补贴,60周岁后,每月发放六七百元生活费,后来还逐年增加补贴数额。不幸的是,一向身体健壮的杨德云,2016年4月6日,在家移栽香椿树劳动中猝死。
兰福林是官庄乡官庄村人,离校后回村务农,后再村里当赤脚医生,挣常年工分。1980年生产队解散后,村医疗室成为私人诊所,他继续当农医。2002年国家允许农医和公办医院的医生一样享受养老保险待遇,他也购买了国家社保公司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60周岁后,兰福林领取了社保公司发放的企业职工养老金,同时还在家继续行医。不幸的是,他给别人治了几十年的病,却难免自己患病。2014年12月,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而亡。
郭春华是蓟县官庄乡塔院村人,离校后回村务农,后来在村内当了赤脚医生,长年挣工分。生产队解散后,村医疗室成为自收自支的合伙经营的私人诊所,他继续在村里当农医。2002年后农医们可以享受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了,他也购买了职工养老保险。60周岁后,他领取了社保公司发放的企业职工养老金,同时还在继续从事医疗工作。
么克民是蓟县官庄乡北后子峪村人,1963年夏季退学回家务农,当时才15虚岁。后来他参军入伍,当了几年兵。退伍后回村务农,他会电气焊技术,在工厂打过工,自己还开过电气焊加工点。后来又在村里承包果树园子,也挣了一些钱。现在虽然步入老年了,仍然在经营果树园。
张连生是蓟县官庄乡西后子峪村人,1965年7月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后学会了裁缝技术,就在村副业组上班,挣工分加提成工资。1980年生产队解散了,他就在家里开办缝纫加工店。由于他缝纫技术高超,成为全乡小有名气的缝纫师。在附近村子收了很多活,平时很忙,收入颇丰。尤其是春节前农历腊月,收活最多,每天都要起早就开忙,晚上还要加班干到深夜,的确很劳累。当然收入也不少,家宅建设的也很好。遗憾的是,由于对国家实行的农民养老保险政策与社会上推销的各式各样的商业保险识别不清,未及时购买国家的农民养老保险。等后来明白过来为时已晚,只能享受老年费的补贴了。
秦树余是蓟县官庄乡东后子峪村人,1967年毕业离校后回村务农,1970年1月参军入伍,1976年夏退伍回村。因他妻子在县医院上班,在城里县医院家属院安家了,他也未到生产队去干农活,而是在供电局做合同工。那时的合同工还没有转正式工的希望,为了多挣钱,他在1983年后,又自己买车,一直开出租拉客人挣钱,收入比打工要多些。他在年满60周岁之前,购买了农民养老保险。年满60周岁后,每月领取社保公司发的农民养老金,同时还继续开出租车。66岁以后,他就不再开出租车了,在家休息。
刘忠贤是蓟县原逯庄子乡(2002年并入城关镇)仓上屯人,离校后回村务农。他们村有果树园子,他当过林果技术员。生产队解散后,他一边耕种土地,一边经营果树,有苹果、柿子、红提葡萄等,他经常到县城里出售水果。2007年国家开始实行农民购买养老保险政策时,错过了机会。60周岁后领取了国家的老年费,现在还在继续经营果园。
刘长泉是原逯庄子乡夏庄子村人,离校后回村务农,在生产队当了农业技术员。他们村在于桥水库北岸,除了种地、种菜、果树园之外,还可以打渔捞虾卖钱,可刘长泉一直以种地为主业,没搞其他副业。步入老年后,领取了国家的老年费,在家里照看孙子孙女,做些轻松的农活颐养天年。
古宝春是原逯庄子乡东大屯村人,1965年7月毕业后回村务农。他在干农活之余,学会了屠宰技术,就在家里杀羊在大集上卖羊肉。生产队解散后,在经营自家土地的同时,在家经营杀羊卖肉的生意,一直干了20多年。后来儿子成年了,父子还开办过家庭小工厂,生产和加工一些小产品。2003年后为自己购买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60周岁后领取了国家社保公司发放的企业职工养老金,还在给城区的一个钢材销售场地当门卫。
王瑞庆是原逯庄子乡西果园村人,1965年7月毕业后回村务农,当过几年村干部。后来抽调到逯庄子乡建筑队当会计,挣工分加补贴工资。生产队解散后,乡建筑队成为独立的小集体所有制企业,他们就改为挣工资了。后来乡建筑队改制解散,被个人承包,王瑞庆就自己创业了。他养过大汽车跑运输,开过晶糕(山楂糕)加工厂等。年近五十岁又被上级要求回村当干部,担任多年的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会计等职务。年近七旬时卸去村干部重担,在家里颐养天年。
李文是蓟县原逯庄子逯庄子村人,1965年7月毕业后回村务农。逯庄子村位于于桥水库北岸,村里有捕鱼队,负责在水库里打渔捞虾。李文也成了捕鱼队的成员,除了挣工分之外,还可以挣些提成工资。1980年生产队解散了,没有工分了。捕鱼队也解散了,打渔的社员就自家购渔船渔网打渔卖钱了。李文在年轻力壮时就一边种地,一边打渔。到年龄大了,不再适合打渔了,积攒的钱也够花了,就在家经营土地了。逯庄子村里土地不多,现在农村耕种收割全部是机械化了,经营那点口粮地也不那么辛苦劳累了。2007年错过了购买农民养老保险的机会,现在领取了国家发放的老龄补助费,在家轻轻松松的过着田园生活。
苏中山是蓟县原翠屏山乡苏庄子村人,离校后回村务农。苏庄子位于于桥水库大坝前面南侧山脚下,是个依山傍水风景秀美的地方。村里除了种地,还发展了养鱼、果树等副业。2012年后,蓟县把于桥水库南岸的几十个村全部拆迁到蓟州东南片新城区内的高层楼房居住,苏中山他们村也拆迁了,都搬到新城区的楼房里去了。现在,苏中山也和城里退休的职工们一样,在新城区里过着休闲的城市生活。
孟庆仓是蓟县城关镇上埝头村人,1965年7月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上埝头是于桥水库拆迁村,村里耕地少,社员们经常到城区的厂矿去打工,往生产队交钱记工分。后来生产队解散了,社员们以种地为辅,以打工为主。孟庆仓就是这样一边务农一边打工,与上班的职工相比,经济收入也不低。1990年后,蓟县的矿泉水开发销售量日益增加,孟庆仓又开办了送水站,专门给各用户送售桶装水。2012年后,蓟州新城区建设中,老县城西部十几个村庄全部拆迁,搬入新建的高层楼群中。现在,孟庆仓还在经营送水站,也和城里的职工一样,过着休闲的城市生活。
高永才是蓟县城关镇小刀剪营村人,提前离校回村务农。小刀剪营村位于城西五名山下,既有水田、旱地,还有山场。高永才回村后,在村里当过干部,还开办过石料厂。后来为了加强环境保护,石料厂停产了,他又继续在村里当支部书记。不幸的是,2014年他得了半身不遂的瘫痪病,2015年初冬病故。
陈余是蓟县城关镇东大井村人,1965年7月初中毕业后回村务农。东大井村是县里的蔬菜种植基地,既有露天菜园子,也有大棚菜。陈余在生产队当了农业技术员,也是村中的生产骨干。在计划经济时期,社员们的收入也比较高。生产队解散后,菜地分到各家各户,陈余家也就成为种菜专业户了。陈余在家种菜,经济收入也比较高,不必外出打工。不幸的是,他在2011年冬,因患病医治无效病故。
顾青是蓟县城关镇黄庵子村人,1965年7月毕业后回村务农。黄庵子村也是县里的蔬菜种植基地,顾青就在村里种菜,也是生产队的农技员,农业生产中的骨干。生产队解散后,菜地分到各户,顾青凭着娴熟的种菜技术,成了种菜专业户,经济收入也比职工的工资高。现在,虽然已经步入老年,他还在家里的菜园中干些力所能及的轻松活。
张方是蓟县城关镇杨园子村人,1965年7月毕业后回村务农。杨园子村临近火车站货位站,村里的副业摊子较多,张方回村后就跟着搞副业,挣工分加提成工资。生产队解散后,张方到城关镇的镇办工厂去上班,成为厂里的骨干,从事管理性的工作。后来镇办厂倒闭了,张方就回到家中,或做买卖或打工。挣了些钱,就在自家院内盖楼房,对外出租,收入也很可观。因他在镇办企业上班十多年,也购买了乡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步入老年后,张方就和国家企业职工一样领取养老金,在家中休息颐养天年了。
单学良是蓟县城关镇三岗子村人,1965年7月毕业后回村务农。三岗子村紧靠城边,人多地少,村里也有不少副业摊点。单学良在生产队当过会计,也在副业摊点搞过副业。生产队解散后,他在经营自家那点土地之外,就专门出摊卖小五金。开始是每天骑自行车去追集,后来买了一辆五马力拖拉机,驾驶拖车追集售货。再后来买卖做大了,就在县城南关大街上租房开五金商店。2000年后,把五金店交给儿子经营,自己在村里当会计。不幸的是,平日身体健康的单学良,在2009年8月12日,突发心脏病亡故。
李树庭是蓟县城关镇白马泉村人,1967年毕业离校后回村务农,后参军入伍,服役期满后回村务农。他写字绘画的水平较高,尤其是绘画人物肖像,更是惟妙惟肖。白马泉紧靠城边,搞副业的机会也很多,李树庭也经常凭写画的技术打工挣钱,成家立业。遗憾的是他的自制能力不高,曾二次因刑事犯罪判刑入狱。50岁后身患中风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但生活尚能自理,也可外出散步,后来病情日益严重,现在家里静养。
杨久如是蓟县城关镇西北隅村人,1963年8月退学回村务农。西北隅是城中村,有多个副业摊点,当时他才15岁,被分配到村办的白铁加工组去学习技术。白铁加工俗称“焊铁壶的”,主要用白铁板裁剪制作帖壶、茶炉、煤球炉的烟筒、铁皮的笸箩、簸箕等。白铁加工工艺包括裁剪铁板模块,板块之间用咬口的方法进行连接,盛水的器皿还要把咬口的部位用焊锡密封。杨久如就和老师傅学会了这些技术,在副业组挣工分和提成工资。生产队解散后,杨久如在大街上自己开个白铁加工店。后来他又学会了钻、铆、电焊、气焊的技术,扩大了店内的加工范围。步入老年后,他也购买了农民养老保险,还在继续从事白铁和电气焊加工工作。
李天国是蓟县城内东南隅村人,1963年8月退学回村务农。东南隅也是城中村,既有许多副业摊点,也是县城的蔬菜种植基地。李天国退学时才15岁,就在村里干些轻体力农活,学习种菜和卖菜。生产队解散后,他家分得了菜园子,成了种菜专业户,经营大棚菜。后来,他们有些菜农在自己的菜地里建起了公寓式住房,租给外来打工人员。他们就把收房租作为家庭收入,这比种菜卖菜可轻松多了。现在,李天国领取了国家发给的老龄补助费(目前60岁以上的每人每月95元,70岁以上的105元,80岁以上的115元),还从村里领取老年退休金(目前东南隅村委会发给60岁以上的村民每人每月260元,西南隅村发给本村60岁以上村民每人每月600元),再加上公寓房出租费,收入也不少,过着轻松而富裕的老年生活。
由于已过50年,经过几个老同学的集体回忆,也记忆不全了,加上毕业照片中后面的同学头像模糊不清,有几个同学是坚持到毕业,还是提前退学的,已经记不清楚了,只好用“离校回村务农”来表述。在闫庆华、兰福林、郭春华、刘忠贤、刘长泉、苏中山、王茂金七个人中,应该只有二个人坚持到了1965年7月毕业才离校。
另外,还有情况不明的王文斌和孙文志两个人。
王文斌的父亲是驻蓟县部队的军官,他是跟随他父亲工作调动来到蓟县的,是转学到我们70班的,不到一年时间,他父亲调走了,他又转到外地去读书了,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孙文志是蓟县桑梓乡辛撞村人,他只在我们70班读了一年书,1963年就离开了一中,也不知是转学了还是退学了。
1961年和1962年的粮食低指标时期,蓟县有些农民外出流浪,俗称“盲流儿”,盲目流动的意思。他们到黑龙江的北大荒或者新疆的南疆一代去给当地的农业社打工。那些地方地多人少,粮食随便吃,在全国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那里的农民也没有挨饿。这些流浪的农民到达那些地区后,发现这些地区的农村大多是民国年间从山东、河北、河南等省逃荒来的移民,他们不欺生,见到内地人很亲切。蓟县这些流浪汉很受当地村干部的欢迎,并鼓励他们回家把全家人的户口都迁移过去,为边疆地区增加人口。这些流浪汉回家一宣传,有的亲戚和朋友也就愿意跟着去体验了一下,感觉那里的农村的确比蓟县的条件好。于是,蓟县就有些农民举家迁移,到北大荒和新疆去安家落户了。
孙文志他们家就是在那时迁移到新疆那边去的,他家在大西北的具体情况,村里人就很少知道了,关于孙文志本人到那边是继续上学读书,还是在农业社劳动,以及他成年后的情况如何,我们就不知道了。
现在,据我们初中毕业已经过去五十年了。我们班的这些同学们,已经有李杰、王建国、单学良、吕巨合、陈余、朱俊祥、高永才、兰福林、杨德云、崔合等人先后辞世。仍然健在的老同学们,也进入退休养老的阶段。
回顾我们班这些老同学的人生经历,正如我们在学生时代老师所讲的,回村务农和在外上班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也不决定个人经济生活的贫富。计划经济时期,工农之间略有差别,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农民家庭的收入比职工干部还高。我的这些初中同学们,虽然从业的岗位不同,但都是普通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家庭经济状况也没有太大的差距。在外上班的最高是处级干部,没有“高官”,在村务农的最富的是个体工商户,没有“富豪”大老板。除郭新华在陕西省临汾市退休和定居、王铂在河北省保定市退休和定居、张景悦在天津塘沽退休和定居外,其余人都在蓟县生活。虽然互相之间见面的机会不多,但是三年同窗共读的经历,也是没齿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