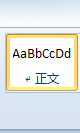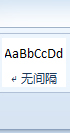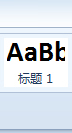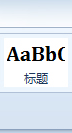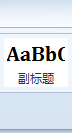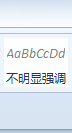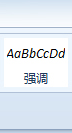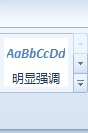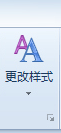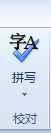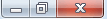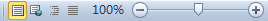到%确定
第9章 婶婶的家
跟着爸妈提着带给叔家的东西走出门来,却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外面正晴空万里艳阳高照,道路两旁是白墙红瓦高高的绿树,蝉鸣肆意的喧嚣着,屋里阴暗压抑,外面却是勃勃的生机。我头一次如此喜欢夏季的户外,即使空气焦灼得几乎扭曲了。
来时路上的人也少了很多,余下的人随着树的影子从西边挪到了东边。离得我们很远,就没再打招呼。径直走进了三叔家所在的胡同。
胡同里坑坑洼洼的过道很不平整,几处踩碎的蜂窝煤铺在上面像一块块补丁。往里望去,挨家挨户大门旁的空地也没有空闲,或是堆着碎砖头,或是种着黄瓜小油菜,稍微富裕点的家庭则紧挨着墙根停放着一辆拖拉机或收割机。余下的空间勉强允许三个人并排行走。
在这个“穷酸”的小小村子里,每一寸土地都得发挥出她的作用。
“就说咱回来准没好事,你看看我说的准不准!你这爹娘还是老样子啊!要是再年轻点,今天还是得一蹦三尺高。”看得出来,自从出了门我妈就开始琢磨这句话了,眼见走远了才终于憋不住说了出来。
没等我爸吭声,接着又说,“恶人自有恶人磨,三儿家是个厉害的,以后有架吵了,看着吧,你这个‘当大哥的’以后少不了‘主持公道’。”
我爸叹了口气,说到底那老两口是他的父母,再不好也由不得我婶婶一个“外人”耀武扬威,就说:“看着就不是个脾气,怪不得和上家离婚了。云霄这么小就跟着她另寻个人家,就不怕孩子被区别对待吗。”
“三儿敢吗?”我妈不屑地甩过来四个字,我爸顿时哑口无言了。
我插不上嘴也不想插嘴。他们这种对话从小就不避讳我,觉得我一个小孩听不懂。可三岁的时候听不懂,十三岁了还听不懂吗?可能在父母眼里,孩子永远是孩子吧。他们告诉我的少说多听多看,我同样用在了这种事上。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也是种人情世故吧,这招我熟。
正想着,爸妈停下了脚步。我估摸着也到了从前的那个老宅子,可眼前“豪华”的大门和我记忆中的老宅大相径庭,让我不禁有些怀疑是不是他们带错了路。
“爸,妈,这是三叔家?”
“这是你三婶家。”我妈意味深长地回了句。我秒懂了她的神嘲讽,忍不住竖了个大拇指:“精辟!”
“什么精辟,你个屁精,人不大懂得还挺多。”我爸笑着拍了一下我的头,侧过头看着我。
他是想看见我笑一笑,可我对“精辟”、“屁精”这个老掉牙的梗实在是懒得奉承,却又不能不给面子:“哈哈,爸,你还挺幽默的。”说罢,便向我妈那走去,逃离他周围名为尴尬的气场。
大门足将近四米多高,让我忍不住想象了一下一米六的婶婶走进这个大门时的场景。稍有些发暗的红漆,金黄发亮的门环,大门两边的石柱子下面一对夜光石狮子贴砖,毫不掩饰的显示着两个大字:就是气派。
大门没锁,直接推门而入。雄厚的金属声响传来,让我不禁感叹这大门的声音真对的起门口那对夜光石狮子。比起爷爷家的大门那牙酸的吱呀声,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进了门,庭院的水准却突然垮了下来。水泥地面本就不平整还起了皮,一辆破旧的拖拉机停放在门洞子里,没了方方正正的外壳,布满油渍的柴油机和硕大的飞轮裸露着,却遮住了画着“花开富贵”的迎门墙。门内的景象让我怀疑三叔家把装修的钱最少八成花在了大门上。
四周红砖堆砌的“东屋”是一个草顶木柱棚子,里面拴着一条雄壮的狗,偶尔传来的“咕咕”声是几只鸽子不甘寂寞的声音。西屋是水泥磨得墙面,要比十年前修缮好了许多,这是我们三口子曾经蜗居的地方。
刮风漏风,下雨漏雨,那时屋顶的唯一作用似乎就是将落在上面的雨水尽量汇聚到一起,方便流进地面上盆子里。那时的雨夜,我爸总是彻夜难眠的,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起来倒掉盆子里的雨水。可纵使生活如此艰难,他却从未惊扰过我一个美梦。
我爸也是有些感慨,似乎时想到了当时破旧的床褥,和两人倒替着穿的破旧衣裳。但他留恋的不是那时的艰苦,而是牙牙学语的我。进门以来我妈的眼神从未在西屋停留,但我知道,越是刻意逃避的越是放之不下。
狗叫声将屋里端坐的人惊动了屋子里端坐的人。三婶放下了手中的杯子,起身透过纱窗望向外面。见有来人便向外迎去。
“哎呀,大哥嫂子来了啊。三儿,快出来接接。在老头子那里呆这么久,可想起来我这了,快进来喝水。”
招牌式的吆喝。